点击阅读英文原文
当大学面临校长工资水平过高的质问时,大学经常强调,他们是在全球市场上选拔顶尖人才。如果你想要证据证明,招聘大学校长是一项无国界的行为,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
例如,去年9月,出生于香港、在美国受训的计算数学家陈繁昌,在管理了雄心勃勃的香港科技大学近十年后,开始执掌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陈繁昌接替了法国土木工程师让·卢·沙梅欧(Jean-Lou Chameo),后者是加州理工学院前校长,而他也是接替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首任校长施春风(Shih Choon Fong),施春风是断裂力学专家,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前校长。
与此同时,今年5月,印度生物学家迪普·塞尼(Deep Saini)宣布辞去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校长一职,担任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校长。6月,出生于英国诺丁汉的心理健康研究员道恩·弗雷什沃特(Dawn Freshwater)自2017年以来一直掌管着西澳大学,她透露,她正要去位于塔斯曼海另一侧的新西兰去就任奥克兰大学校长一职。
另一方面,7月份,结构工程师滕锦光出任香港理工大学校长,除了在30英里外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短暂担任副校长之外,他自1994年起一直在香港理工大学工作。同月,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常务副校长尤妮斯·西蒙斯(Eunice Simmons)被大约75英里外的切斯特大学任命为校长。
今年6月,自2000年以来一直在津巴布韦大学工作的土壤科学家保罗·马普沃(Paul Mapfumo)在担任代理校长近一年后,正式成为该大学的新任校长。同月,夸祖鲁-纳塔尔大学常务副校长、政治学家纳纳·珀库(Nana Poku)在担任代理校长8个月后,正式担任校长一职。荷兰遗传学家西塞卡·威梅加(Cisca Wijmenga)被任命为格罗宁根大学校长,她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格罗宁根大学工作。
事实上,澳大利亚最近就职的9位大学校长中,有8位是从州际大学或机构招聘的。泰晤士高等教育最近对世界400强大学的校长进行分析后发现,有海外学术背景的不到五分之一。
事实上,不远万里,从地球另一端寻找新校长走马上任,更多的时候是例外,而不是常规。一种更为人熟知的做法是,面对校长一职的缺失,大学宣布它正在四处寻找最好的替代者,最终却只能从隔壁的大学——或办公室——寻找继任者。
当然,在一些系统中,大学真的是到处寻找新的领导者。香港就是一个例子,尽管滕锦光最近出任香港理工校长,但其他七所公立大学中,有四所大学的校长是直接从美国引进的。
香港理工大学院校研究与规划处处长艾莉森·劳埃德(Alison Lloyd)说:“我们在招聘校长时,政策是非常开放的,这关系到寻找将大学提升到下一个发展水平所需的技能组合。校长对大学文化细微差别的理解非常重要,同时,还要对更广阔世界中的工作方式有很好的理解。二者要有机结合起来。”
劳埃德说,由于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大学领导阶层不可避免地会交叉融合。“我们有很高比例的教师在海外接受过教育,并且了解土生土长的亚洲文化。香港靠近中国大陆,这一区位优势吸引了许多高水平学者回到香港。”
荷兰则采取另一种做法。很难找到比马斯特里赫特更国际化的地方了。马斯特里赫特是荷兰的一座大学城,坐落在比利时和德国之间的一小块土地上,它的名字来源于欧盟的创始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马斯特里赫特大学以其国际化为荣:大学的许多课程都采用英语授课,50%的学生和40%的学者来自海外。
然而,荷兰大学不但没有从国外招聘校长,甚至避免从荷兰其他大学招聘。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现任校长里安·莱切特(Rianne Letschert) 在2016年的就职演说中指出,她被从大约75英里外的蒂尔堡大学招募过来就任马斯特里赫特校长,这一事件“打破了许多传统……在一些人看来,甚至违反了法律。”
莱切特说,在管理荷兰14所政府资助大学的40多名执行委员会成员中,仅有两人来自海外,其中就包括来自德国的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校长马丁·保罗(Martin Paul)。
“我们倾向于主要任命荷兰高管,这不是一件好事,”她说。“荷兰方式并不总是最好的方式;我更喜欢输入新鲜血液,获得新的洞察力。在荷兰有这么多海外工作人员,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升任管理层?他们是学校培育的好苗子,可是他们永远无法升任最高领导层。”
新加坡的模式处于香港和荷兰二者之间。虽然排名最靠前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有新加坡血统,但其竞争对手——南洋理工大学现任校长是孟买出生的工程师苏布拉·苏雷什(Subra Suresh),他曾是宾夕法尼亚州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校长。苏雷什是接替瑞典生物化学家贝尔蒂尔·安德森(Bertil Andersson)担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一职的,后者是林克平大学的前任校长。
南洋理工大学中国遗产中心前主任纪宝坤(Pookong Kee)表示,鉴于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南洋大学所承载的“特殊文化使命”,这些海外任命“特别引人注目”,南洋大学是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以外第一所用中文教学的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成立于新加坡殖民时期,一直用英语教学,“因为英国不愿意让汉语进入高等教育”。
现任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纪宝坤教授称,招募既没有中国血统也没有新加坡血统的校长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做法,即在领导力方面,血统是无关紧要的。“北京大学现在有一个全球使命,从外界招募最优秀的人才。而新加坡国立大学是全国性的,确实有一些国情上的考虑。”
纪宝坤教授补充道,海外任命的风险在于,这种做法触犯了民族主义情绪。例如,老南洋大学仍然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全球校友网,其中一些人“可能会抱怨任命非新加坡籍人士为校长”。纪宝坤称,我们不知道大学聘任委员会是否考虑到了这一点。我相信官方文件会显示他们任命了最好的人选,而且是通过正当的方式,但是大学通常有自己的优先事项和考虑。”
在一些地方,民族主义可以被地区主义甚至部落主义所压制。去年,两名外籍校长试图将西方行政规范强加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大学校园里,但最终都以逃离该国而告终。
威尔士植物学家约翰·沃伦(John Warren)在位于拉包尔的自然资源与环境大学担任了两年的领导职务后,于今年8月辞职。此前,他决定按照个人才能,而不是对部落的忠诚度来任命一名副校长,这显然引起了校长的愤怒,并招致警方的暗中威胁。
三个月前,荷兰环境经济学家阿尔伯特·施拉姆(Albert Schram)由于试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理工大学根除腐败,最后被迫离开了该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理工大学曾多次试图解雇他,最终校方采用明显虚假的手段,声称他伪造了博士学历,而将他下狱。他在保释期间逃跑了。
但就南洋理工大学而言,前任校长、新加坡人徐冠林表示,南洋理工大学选拔校长,考虑的是候选人的技能,而非文化因素。去年5月,徐冠林在阿布扎比哈里发大学举行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峰会上说:“我在寻找我的继任者时,我在新加坡找不到合适人选。除了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挖走资深人员过来,再也没有其他选择,所以我们不得不寻找外国人。”安德森(Andersson)最终接替了他。
徐冠林表示,国内选择面窄,要归咎于新加坡的一贯做法——利用奖学金迫不及待地吸引海外博士后研究人员回国。他在峰会上说,这是一场“成功的悲剧”,因为拥有大好前途的新加坡人失去了在海外发展学术技能的机会。“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还有决策者和研发主管。”
一个例子是南洋理工大学新校长苏雷什(Suresh),他在美国担任了三年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徐冠林说:“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培养这样的人才,这需要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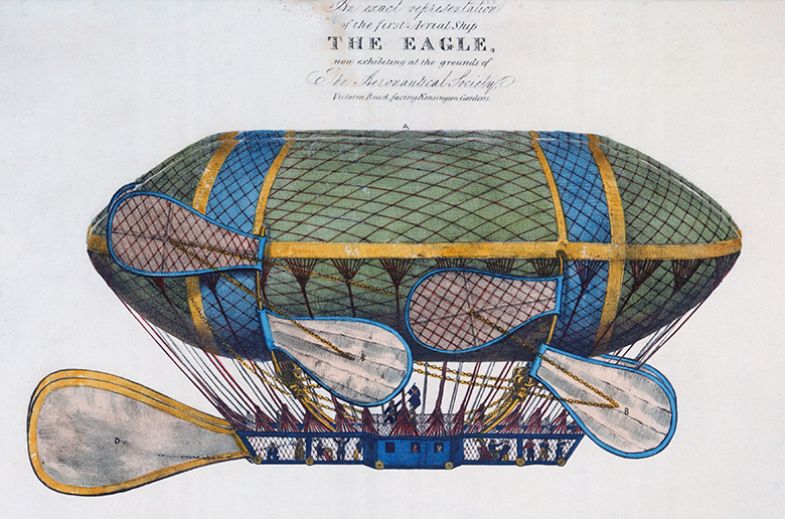
如果说南洋理工大学向西方国家寻找新校长,那么其他大学也在从东方国家寻找。陈繁昌说,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而言,这种情况从大学“成立之初”就是如此。2008年,首任校长施春风就是从新加坡招募而来的。
陈繁昌在去年的世界学术峰会上表示,沙特阿拉伯传统上“非常西方化”,尤其是从美国那里汲取了经验。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行的世界学术峰会上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到美国,而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但现在最大的人才基地在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你试着向最优秀的人学习,而不是试图模仿某个国家或地区。沙特阿拉伯,尤其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必须放眼东方,因为……人才就在那里。”
陈繁昌根据自身经历补充道:“当今世界高度全球化,十年前我回到了香港,但现在我已经离开了。我离开是因为我讨厌香港吗?不,而是因为我找到了更好的机会。人往高处走,无论你身处何方,这都无法避免。”
北京大学的纪宝坤指出,大学经常请大型国际招聘公司来帮助填补高级职位空缺。这些公司可能总部设在伦敦或美国,它们的数据库在国籍方面可能“向某些方向倾斜”。由于大学校长通常从教务长、院长和其他高级行政人员中挑选,这些级别的选拔模式可能会在选拔校长时中重现。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教育家、墨尔本大学前校长李光昭(Kwong Lee Dow)指出,大学校长足迹遍布全世界,他们自己也可能偏向某些领域。例如,医学、卫生和科学领域的学者流动性极强,大学不太可能由学术背景过于窄(如法学)的外国人领导。
就香港而言,李光昭指出,大学领导模式有所波动。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之前,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老牌大学倾向于从香港本地招募校长。像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等年轻大学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更名为大学,从一开始就有更多的中国人担任“要职”。“他们通常是中国人,曾在西方大学(通常是英国国家大学)长期学习并担任教职。”
尽管新加坡对外国大学领导人的开放程度不如中国香港,但二者与东亚大国均形成鲜明对比。李光昭表示:“在中国的著名大学里,很少有外国人身居要职,当然更不会在日本的大学里出现这种情况。”
李光昭也曾担任维多利亚州巴拉瑞特大学的校长,他是为数不多具有中国血统的、并在澳大利亚大学做到校长职务的澳大利亚人。“时不时会有来自亚裔担任主管国际关系或科研的副校长。但实际上,就澳大利亚大学现在的领导层构成而言,多元化程度可能还不够。”
李光昭希望,这种局面会在未来5至10年发生变化。他表示:“就像现在人们对让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认识有所提高一样,我认为有一天会出现不同种族的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情况”,尤其是在墨尔本和悉尼等大学云集的大都市。
李光昭表示,尽管亚裔澳大利亚人不会对大学领导层的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但他们将更好地反映当代澳大利亚社会的结构,并将进一步改变“人们对人员配置和任命的看法”。担任这些职位的人可能在东西方国家都有相当多的国际经验。你会发现在澳大利亚出生并接受教育的具有中国背景的人,在东方国家获得一些经验,然后回到澳大利亚担任领导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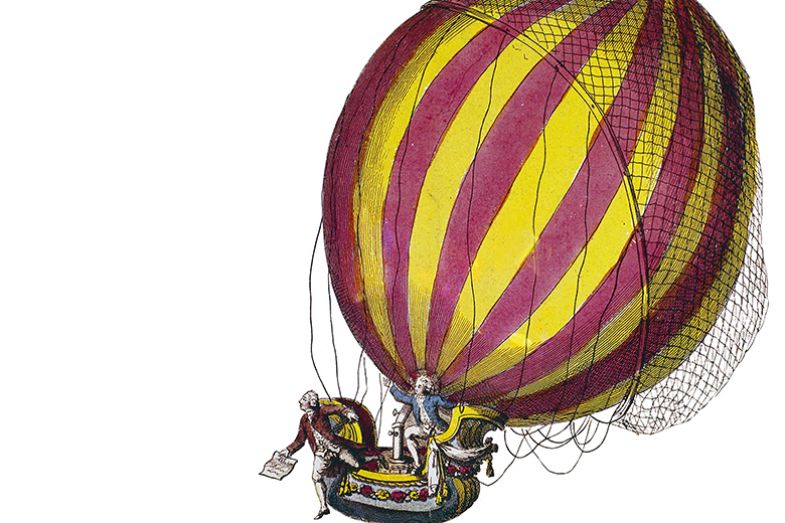
如果一个来自少数民族的大学领袖能够激发灵感,那么弱势群体领袖的象征意义就更加重要。南非黑人数学家马莫克吉·帕肯(Mamokgethi Phakeng)去年成为开普敦大学的校长,上任时,该大学在学费和帝国主义的痛苦冲突中挣扎,他说,区分“和平时期和危机时期”很重要。
帕肯说:“每个实体在招募领导者时都必须清楚:当下的背景是什么?我说的背景不仅仅是医院、教育机构或其他什么机构类型。而是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你必须任命一位适合的领导人。在南非目前的危机中,如果有人不了解社会和政治背景、辩论、高等教育和当地的竞争,要想胜任大学校长一职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这并不是说局外人能力不行。和平时期的优秀领导人在危机时期失败,并不一定就是个糟糕的领导人,只是因为他们的领导力在危机时期行不通。”
帕肯坚持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南非的大学应该逃避国际化。“你仍然竭尽所能,想从世界各地招募人才。”但是,在南非这样一个为身份问题和纠正过去而挣扎的国家里,会有一些限制,如“学生在大学里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学生认可大学的教师、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吗?如果大多数人来自国外,这样的问题可能很难解决。”
开普敦的前任校长、约翰内斯堡出生的医生、罗兹奖学金获得者马克斯·普莱斯(Max Price)同意“背景意味着一切”这一说法,大学在不同的时间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力。他认为,八年前,即在2008年被任命为开普敦大学校长之前,他“不会也不应该”被授予校长职位。当时,开普敦大学已经被前任校长“翻了个底朝天”,需要有人“让大学平静下来”。
“否则我可能会犯错。我想追求一种愿景,并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当开普敦大学准备好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时,我碰巧加入了,这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
西澳大学校长弗雷什沃特(Freshwater)表示,外部任命带来了一个特殊的视角。她说:“当我来到西澳大学时,我不知道我得罪了哪些人,有些人的利益链很长。但是我知道需要做什么。过去六年里,这所大学发生了建校110年来最大的转变,真是喜忧参半。”
弗雷什沃特承认她的方法并不总是得到认可。“有些人认为,像我这样的外来人士让大学失去了灵魂。人们有一种假设认为,无论是内部选拔,还是外部聘任的校长,都很难做出改变。”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校长莱切特说,背景也可以决定中层领导的选择,比如院长。“你未来几年的战略是什么?如果大学需要地区结盟,我会选择了解该地区的人;如果大学对外开放,我会选择一名顶尖的国际人才;如果我们需要在海牙进行更多的游说,我会选择了解首都政治规则的人。这实际上取决于大学所面临的挑战。”
但是,斯图加特大学校长沃尔夫拉姆·雷塞尔(Wolfram Ressel)认为,大学领导人的招聘人员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只要任命外国人,就会促进大学的国际化。这是因为,在当今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年代,“每个学术机构都在以全球化的方式思考问题。在德国,主要的研究型大学都在以全球化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我们从来不仅仅在全国范围内思考。”
虽说如此,可普莱斯发现,很难想象一个“局外人”被选为德国大学的校长。他说:“与政治、政治家和当地利益攸关方接触;对高等教育系统和科研基础设施运作方式的深刻理解;筹集资金,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当地,并依靠关系网络来推动——所有这一切都给本土候选人带来巨大的优势。”
但身为国际律师的莱切特认为,管理大学的复杂程度有时被夸大了。她质问道:“如果我花时间学习和倾听,管理一所澳大利亚大学真有这么难吗?”
在她看来,全世界的学者都面临着相似的课题和挑战。“我想一个人需要半年时间,才能真正了解一所大学。也许并不是了解大学文化——这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有外人的参与也会让人耳目一新。”
着眼于提升排名的大学,也可能想考虑顶尖大学校长的背景。在香港,排名201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前四位的大学,校长是直接从美国招聘的。在澳大利亚,排名最高的四所大学中,有三所大学的校长都在国外出生,第四所大学的校长是一名澳大利亚人,他是回到自己的母校担任校长一职。世界排名前四位的大学,校长都是海外出生。
当谈到学术成功时,人们很难将原因与结果区分开来,但这些数字很可能会让大学董事会停下来仔细思考。全球领导人才市场也许被夸大了,但那些敢于大胆尝试的人可能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后记
Print headline: Should universities look overseas for their top recruits?








